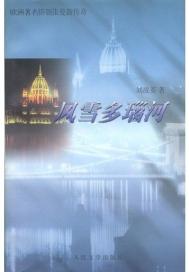桃子出事了。
马其鸣跟袁波书记正在激烈争论郑源的事,突然接到李春江电话,说是桃子死了。
案是李钰那个叫小彬的助手报的。这天下午,小彬抽空又来到桃子家,这段日子,只要有时间,他就往桃子这儿跑。桃子是他表姨,又是她私底下把他推荐给李春江,心里,他是很感这份情的。
小彬敲门进来时,桃子像是要出门,她的神色很异常,风衣扣子系错了都没发现。小彬故作轻松,说:“表姨啥事儿这么紧,看你,扣子都没系对地方。”桃子脸一红,进了洗手间,对着镜子重新整装去了。
小彬心里涌出一股不祥,其实这种不祥早就有了,只是从没这么强烈。表姨一向是个很注重仪表的人,要不遇啥紧迫事儿,绝不会粗心到这程度。再说她提的那个包,小彬像是从没见过,比平日提的要大,也粗糙,一看就是地摊上买的便宜货。这更不符合表姨的习性。小姨是个在包上很讲究的女人,这点上小彬记忆犹为深刻。刚到李钰手下,他曾给表姨买过一个包,是在省城名牌店买的,花了他半月的工资。谁知桃子拿手里一看,便说这包太俗,没一点儿个性,弄得小彬当时很尴尬,六百多块钱的包她一次也没提过。
桃子整好衣衫走出来,问小彬:“有事?”
小彬说:“没事,路过这儿,上来看看你。”
桃子显得很不自在,站在那里,不知道言说什么好。很明显,她急着要出门,小彬却故意赖在那里,装作反应不过。其实小彬有自己的想法,自从负责康永胜的案子后,他心里一直替桃子担心,但又受纪律约束,不能把实情告诉桃子。这段时间,他暗中调查,终于查到了那个叫黄大伍的男人。这家伙现在牛逼得很,穿几千块钱的西装,抽中华烟,整天不是出入酒楼就是在夜总会厮混。小彬找到这阵子跟黄大伍关系很蜜的坐台小姐芳芳,从她口中,知道黄大伍敲诈过桃子,而且不止一次。听芳芳的口气,黄大伍压根儿就没打算放过桃子,他跟芳芳说,这么好的一棵摇钱树,老子能丢开?芳芳还说,黄大伍垂涎桃子的美色,她们做那事的时候,就听黄大伍喊出过桃子的名字。黄大伍不止一次说,能尝尝县委书记老婆的滋味,这辈子也值。
小彬担忧,桃子会不会为了郑源,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他很想跟桃子暗示一下,马其鸣已经在着手调查此案,弄不好,郑源真会翻船,到那时,桃子可是人财两空。
见小彬磨蹭着不走,桃子说:“你先看会儿电视,我跟同事约好了出去,不能让她等太久。”
小彬不能再赖下去了,不好意思地站起身,说:“我也要回去了,晚上还要值班。”小彬在楼下一直看着桃子上了车,才在心里骂自己,为什么不告诉她,是纪律要紧还是表姨要紧?
桃子果然是去见黄大伍。而且这一次,她是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两天前的晚上,黄大伍将她叫到宾馆,见面没几句话,就开始动手动脚。起初桃子忍着,知道要救郑源,迟早得过这一关。黄大伍现在已不跟她提钱了,他的眼神**裸地告诉她,他想得到的,是她的肉体。桃子甚至暗想,如果这样能救得了郑源,她情愿豁出去,就当被歹徒**了一次。这么想着,她的身体放松下来,不感觉到黄大伍那么恶心了。黄大伍那只戴着金箍子的大手试图侵犯她的酥胸时,她努力着将目光避开,扭头去看窗外的山景。秋末的子兰山一派红艳,只是那红,带着一股血腥的味道。黄大伍见她顺从,乐得双手一起扑向她,只几下便撕开了她的胸衣,贪婪的双手就像玩泥巴一样狠狠捏住那对美丽的**。桃子疼得叫了一声。有了钱的黄大伍已不像过去那么没教养,也远不及以前那么猴急,大约在风月场中他也找到了一些如何挑逗女人的经验。那么粗俗的一个人竟玩起细活来,这令桃子更不可忍受。如果姓黄的能像强奸犯一样草草收场,兴许那天她也就把这事儿给了了。长痛不如短痛啊,桃子真是让长痛折腾够了,再也不想忍受下去了,她心里祈盼着,如何咔嚓一声,把这事儿给彻底了断掉。如果真能这样,再大的屈辱,她也就受了。可惜姓黄的不这么想,姓黄的想细细玩,慢慢玩,玩县太太毕竟跟玩小姐不一样,机会难得,说啥也得好好珍惜。
那天桃子最终没让姓黄的得到实质性的快乐,就在姓黄的想解开她下面的衣服时,她狠起一脚,差点将姓黄的踢成阳萎。姓黄的抱着下身跪在地上,半天才发出一声:“你狠啊!”那一刻,桃子真有一脚踹死他的冲动。
今天,姓黄的又一次打电话,还是那家宾馆,姓黄的说,如果再敢踢他,他就一脚把郑源踢到监狱。得了结了,不能无休止地拖下去,也不能无休止地让人纠缠。这种日子她过够了,再也不想过了。她做了最坏的打算,也做了最好的打算,就看姓黄的自己怎么选择。
这一次,姓黄的果然表现得很不一般,甚至有了一种城里男人的风度。大约他也摸透了桃子的心理,知道机会不再,所以想表现得大度而又文雅一点儿。桃子一进门,他便热情迎坐,还问了句:“路上没堵车吧。”这话桃子听得怪怪的,姓黄的啥时学会说人话了?她坐下,将包放脚底下,姓黄的问:“是喝水还是来杯饮料?”听听,这口气哪像个魔鬼,分明是绅士。桃子没心情听他虚情假意,问:“我说的话你考虑得咋样?”
桃子在电话里说:“你不就图那个吗,行,我给你,横竖就这一次,但你得拿出实质性的保证来。”
“我保证,我保证。”姓黄的连说了几个保证。
“怎么保证?”
“我发誓,我发毒誓,要是以后再纠缠你,让车撞死,这总行了吧?”
桃子哼了一声:“你这叫誓?你这叫屎!”说着,扔给姓黄的一沓照片,“你看看,你仔细看看。”姓黄的捡起照片,一看,厉声惊叫起来:“你哪来的?”
桃子冷冷地道:“我告诉你,这样的照片我有很多,你若再敢纠缠我,这些照片会送你到该去的地方。郑源我不管了,该坐牢坐去,可你别忘了我是谁,收拾你黄大伍我还是绰绰有余!”
黄大伍惊了,愣了,没想到桃子会来这一手。照片一半是他跟芳芳行那事的,他的脸清清楚楚,倒是芳芳有些模糊。还有几张,是他将老家来三河打工的一小女孩哄骗到宾馆诱奸的镜头。女孩后来喝了毒药,差点死掉,想不到这么隐秘的事儿桃子也能拍到手。黄大伍大睁着双眼,惊恐得不敢相信。
“你……你……?”
“黄大伍,你想清楚,那女孩现在在我手上,只要我乐意,一个电话就能送你进监狱!”
黄大伍结舌得说不出话。他这才发现,面前的女人不是他想得那么简单,也不是晚上躺床上臆淫时想得那么缠绵。“好,好,我听你的,你说咋就咋……”
“听着,”桃子看着这个狠琐而又无耻的男人,声音里突然有了力量,“你马上离开三河,滚到该滚的地方去。再敢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黄大伍傻在那里,像是让人突然拿刀给阉了。
桃子不想再跟这个可憎的男人纠缠下去,提上包,起身往外走。就在桃子伸手开门的一瞬,黄大伍突然从梦魔中醒过来,狼一般扑过来,一把抱住桃子。“臭**,想走,没那么简单!”黄大伍边骂边用力卡住桃子的脖子,使足全身力气,猛地将桃子扔回床上。桃子还想反抗,黄大伍已从床下拿出一根绳子,恶狠狠地瞪住她,“臭女人,你以为你是谁,敢吓唬老子,老子今天让你死!”说着,狼一样扑向桃子。桃子被他猛然一击,心跳得接不上气来,双手抚住喉咙,正要缓气儿,黄大伍的身子便压了过来。
黄大伍此时已是穷凶极恶,什么也不顾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干死她!两人扭在一起,桃子哪是黄大伍的对手,没几下,胳膊和腿便被黄大伍牢牢地捆住。挣扎中,她的衣服被撕开,头发成了帮凶,黄大伍一手撕着她的头发,一手扇着嘴巴,边打边问:“还敢跟老子讲条件吗,还敢拍老子的照片吗?”
血从桃子嘴里流出,后脑勺也在床头上磕破了,桃子感到那儿一片湿热。她强撑着,使出全身的劲,用力朝黄大伍撞去。黄大伍轻轻一闪,桃子重重摔在地毯上。
接下来,黄大伍可以缓和一下神经了,这个丧心病狂的男人,此时已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看着像羔羊一样倒在地上喘息的桃子,脸上露出一股狰狞。“你不是不让老子干吗,你个臭**,跟老子玩心眼,老子今天让你见识见识,到底谁狠!”说着,他扒下裤子,扔掉衬衣,将桃子摔到床上,凶狠地扑了上去。
桃子死死地闭上了眼睛。一阵剧痛后,桃子失去了知觉。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僵死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桃子再次睁开眼,黄大伍不在,一片哗哗声从洗手间传来,这个畜生,大约是发泄够了,钻洗手间洗澡去了。桃子全身疼痛,翻不过身。还好,身上的绳子解开了,大约黄大伍看她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想松开她好好尽兴一场。桃子摇了摇头,终于弄清眼前的现实,目光顺着身子,清晰地看到黄大伍留在她身上的大片罪恶的污渍。她几乎没再怎么想,其实也用不着多想,仿佛结局早就摆在了那里。她挣扎着下床,艰难地打开包,然后,**着身子朝洗手间走。
黄大伍听见响,刚从洗手间探出身子,就感觉一把冰凉的刀子刺进自己的某个地方。他惊异着,有点不敢相信而又急切地从蒙蒙水汽中找回目光,就看见无数把刀子从空中舞来,一刀一刀的,在他刚刚清洗过的身子上扎开了花。鲜艳的花,罪恶的花,美丽的花,黄大伍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便软软地跟血融在了一起。
小彬真的在值班,按照马其鸣的指示,康永胜目前羁押在三河看守所,除小彬外,马其鸣又从别处抽来两名警察,对康永胜的审讯,必须三人同时在场才能进行。可康永胜像是受到某种启示,再也不提李欣然交代过他什么事了。审完康永胜,又对笔录做了最后核对,已是夜里十点四十。三个人争嚷着由谁请客,去吃夜宵,小彬忽然就想起表姨。往桃子家打电话,没人接,打她手机,电话通着,却不接线。小彬紧张了,一股不祥袭来,扔下两位同事,就往桃子家跑。门紧闭着,小彬敲半天,里面没一点儿动静。再打手机,还是不接线。惊慌中他蓦地想到黄大伍,马上打电话给芳芳,问黄大伍在什么地方?芳芳犹豫了下,告诉了他宾馆及房号。小彬赶到那儿时,桃子死了已有半小时。
马其鸣和李春江一前一后赶到宾馆,重案二组的警员正在清理现场,负责指挥的正是老陈。老陈告诉马其鸣,桃子是自杀,她在黄大伍身上刺了二十六刀,然后用刀割断了自己的动脉血管。
李春江脑子里嗡一声,险些栽倒在地。
马其鸣什么也没说,看得出,他的震撼绝不在李春江之下,但他坚强地挺住了。看着警员们将桃子的尸体抬走,马其鸣走过来,轻轻扶住李春江的肩膀。这一刻,他有太多的话想跟这位战友说,谁知李春江突然抽出身子,理也不理他,追着桃子的尸体而去。小彬几个也扔下马其鸣,紧随李春江而去。弥漫着悲怆味的楼道内,马其鸣的影子有点孤单。郑源正在乡下检查工作,猛接到消息,腿都软了。巨大的噩耗如同晴天霹雳,重重地将他击倒。等吴水县委的同志将他搀扶到殡仪馆时,那儿的悲痛已化作一地凄凉,风卷着朵朵撕心的哭声,将他烂了一次的心再次撕烂。
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悲哀似乎在瞬间笼罩住人们的心灵。马其鸣默默地站在风中,任初冬的寒风坚硬地刺穿自己。风中似乎飘荡着袁波书记的声音:“不能这样做,我不能看着一个好同志被你们送进监狱,那对吴水、对三河,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他似乎再一次触到李春江充满怨恨的目光,尽管那目光有些无奈,有些迫不得已的深藏,但恨却是明显的。就在刚才,李春江还跟他发火:“这案子还有啥办头,我连自己的朋友都保护不了,还当哪门子公安局局长?”
是不是真有些过分了?这样做是不是真的不近人情?难道真像梅涵所说,我现在成了办案机器,变得残酷、冷漠、自私,没一点儿人情味?就连十六岁的朵朵也在怪他,边哭边冲他发火:“你走开,桃子妈妈不想看到你!”望着被悲痛袭击得东倒西歪的桃子的亲人和同事,马其鸣第一次流下了酸心的泪。
风还在吹,初冬的风,坚硬、冷漠,有刀子的质感。
吴达功还是那么顽固。
所有进去的人,一个个都招了,就连范大杆子,也终于张开了那张被石膏封上的嘴。
案情已彻底明朗,范大杆子承认,他是二公子的人。他从部队回来不久,便被毒枭马青云看中。马青云被老曾丢进法网进而被枪毙后,他便接管起二公子这片事业。据范大杆子交代,二公子做这事起步比大公子晚,发展却很猛,眼下已控制了西北五省一大半市场。主要贩卖***、***和**。进货渠道在广州和**,顶头老板是一个叫福爷的港商。范大杆子主要替二公子打理本省业务,偶尔也陪二公子到外面走一遭。至于二公子势力到底有多大,范大杆子无从知晓,他只晓得二公子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外表根本看不出他是干这行的人。他在省城的产业多得自己都数不清,常常是下面的人跑来跟他报告利润,他才略作惊讶地说:“我还有这么一份家业?”
他迷恋这个。范大杆子说,他老子也拿他没办法。
范大杆子交代出一个重要情节,他们在沙漠农场啥也没干,就养着一群羊,孙吉海老婆的羊。老曾听得糊涂,质问啥:“也没干为啥搞那么神秘?”范大杆子笑笑,说:“神秘?你也觉得我们神秘?”老曾让范大杆子的口气激怒了,一不注意就给了他一耳光。范大杆子警告老曾:“再打我控告你。”老曾又扇了他一个耳光,斥道:“我让你控告!”这下范大杆子老实了,他知道老曾是个不大受纪律约束的人。这种人一把他约束起来,灵感就没了,等于是废人。很遗憾,李春江没在他头上套紧箍咒。
范大杆子不服气地说:“就许你们有策略,不搞那么神秘,孙吉海能听二公子的?”
老曾一拍桌子,说:“娘的,让这帮狗日耍了!”
范大杆子开心地笑笑,这时候他还能笑得出来,可见他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说,周生军怎么死的?”老曾真是服了这家伙,他身上,的确有股子江湖气。
范大杆子跟老曾讨了根烟,吸一口说:“还能怎么死,我让人做的。”
到这份上,范大杆子已不打算有保留,反正也活不了,不如痛痛快快说了。他如实交代了派人杀害周生军的经过。原来,李春江他们对沙漠农场采取措施后,警方的一举一动都在范大杆子的监控下,监控沙漠农场的那几个人都得过他好处。直到后来,他们怕警方真将周生军抓回去,那样,这儿上演的空城计就会露陷儿,于是范大杆子抢在警方作出反应之前,派人将周生军骗至沙漠,活活丢进了枯井里。这小子,不但蒙骗了警方,也牢牢蒙住了孙吉海的眼睛。
所有证据面前,吴达功还是不开口。案情分析会连续开了几次,面对顽固不化的吴达功,一时谁也显得智慧不够,大约他太懂得口供的厉害了,所以决心硬到底。
综合所有形势,马其鸣决定将贩毒案移交省厅,集中精力对三河政法系统腐败案展开彻查。就在范大杆子被移交到省厅这天,三河市作出一项重大决定,正式逮捕全国劳模、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优秀企业家童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