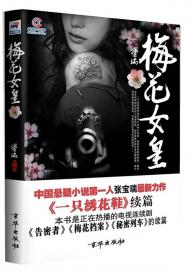序一
“六W”与“三结合”
梁羽生
一
文章贵有个人风格,对长篇小说而言,更是如此。无风格不能成家。——虽然成家的条件不止一种,但风格却是属于基本的因素。
张宝瑞的武侠小说是有他的个人风格的。我和张宝瑞不相识,只知他是记者“出身”。作家的风格往往受自身经历的影响,张宝瑞的风格似乎也是源于他的职业。
西方新闻界有“六W”之说,把一篇新闻报道必须具备的因素概括为when(何时)、where(何地)、who(何人)、what(何事)、why(何故)、how(如何)。此说虽来自西方,但中西一理,若缺少其中之一,就不能成为一篇完整的新闻报道了。
张宝瑞的武侠小说具有纪实文学的性质,在大陆亦早有定评。以他的两部代表作《醉鬼张三》和《八卦掌董海川》为例,前者写三皇功创始人张长桢的一生,后者写八卦掌开山祖董海川的事迹。书中的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是真有其人,实有其事的。纪实文学脱胎于新闻报道,其必须具备“六W”,是无须说的。
除了真人实事之外,张宝瑞还有严格的时空观念。例如《醉鬼张三》十三、十四两回,写了张三在某年春节期间的活动:闹花会,看艺人的杂耍;逛厂甸,听小贩的吆喝;游鸟市,赏珍禽的奇姿;进戏园,观名伶(杨小楼)的演出……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清末民初的北京民俗画卷。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描绘,是决不能移用于别的地方、别的年代的。
最后两个“W”(why, how)属于叙事的范围。任何小说都离不开叙事,因此只有技巧高下问题,并无需不需要问题。技巧问题,在有限的篇幅中是难作评述的。
是否必须具有“六W”,要看作品的性质。例如历史小说必须有,科幻小说就无须了。武侠小说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只是“成人的童话”;因此,是要“六W”具备,还是只要其中的一部分,那就全看作者的取向了。尽管许多武侠小说说不清楚故事发生于何地何时,但自有其文学价值,正如“成人的童话”一样。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有“六W”的作品,因为出于高手的“成人童话”固然有其文学价值,但若是粗制滥造的作品则难免令人有云山雾罩之感了。
二
有了个人的风格,还得有坚实的内容,否则就不耐看了。有如千娇百媚的美人,其魅力也终如彩云之易散。
张宝瑞的小说是够得上用“坚实”二字来形容的,尤其在“武”这方面。他写的是名副其实的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用简单的算式表示,即:武 侠 小说。必须三者结合,才能名实相符。
并非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有武有侠的,早就有人指出一个现象:“许多武侠小说都是有武无侠,甚至武也没有,有的只是神,神怪的神。”
张宝瑞的小说,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关武术的描写,大陆作家林斤澜就这样说过:“现在的文坛有两怪,一是张宝瑞,专写武术;二是柯云路,专写气功。”《八卦掌董海川》第十五回,张宝瑞写董海川与铁佛法师谈论武术,对各门各派的拳脚功夫如数家珍。张宝瑞的武术知识之广博,于此可见一斑。
张宝瑞的小说有侠,无须待我来说。他那两部代表作的主角——张长桢与董海川,本来就是有许多行侠仗义事迹在民间流传的真实人物。
张宝瑞的武侠小说有纪实文学的性质,但并不等同侠士的传记。他还是用小说的手法写的,有在特定环境中“可能发生”的虚构情节,也有为了突出主角形象而安排的次要人物。当然,也有人物的刻画和气氛的描写。
三
对于武侠小说的“三结合”,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因为在认同者中也还有枝节的差异,何况还有不认同的呢,这里无法作深入的讨论,只能略抒己见。
首先,在“三结合”中,哪一样是重要的?当然应是小说。武侠小说不能写成传记,更不能写成论文(有人指出,我有几部小说犯了说理过多的毛病。这确是我应作自我检讨的)。这一点似无异议,问题只在于小说写法的讨论了。例如小说总有叙事(武侠小说更加是以讲故事为主的),那么用什么人的眼睛来做见事之眼呢?用作者的眼睛还是用书中人物的眼睛?我比较倾向于用人物之眼。对于“三结合”,我个人的排列式是:小说、侠、武。
武侠小说必须有武,这一点似乎无异议。不过,是虚写的好还是实写的好,就有不同的意见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取向问题。扬长避短,是任何作者都会选择的道路。例如我,因为不懂技击,也不懂气功,就只能虚写了。但我总觉得欠缺这方面的知识是一大憾事。
最大的分歧在“侠”这一方面。有人认为“侠”的观念早已过时,不合潮流。武侠小说若受侠的观念束缚,就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性。
对于“潮流”,我不会视而不见。今年四月间,我在北京写的一首小诗,开头两句就是:“上帝死了,侠士死了!”
“侠气渐消”这一社会现象,恐怕亦非自今日始。一百五十年前,龚自珍就发过“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舟中读陶诗三首》之一)的感慨。还有别人(清末文人吴伯揆)集龚诗的对联:“侠骨岂沉沦,耻与蛟龙竞升斗;人事日龌龊,莫抛心力贸才名!”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武侠小说必须有侠,否则干脆取消那个“侠”字,叫做武打小说或别的什么小说好了,何必“挂羊头而卖狗肉”。至于有侠就会损伤艺术性,我也不能同意。写得不好,那只是手法高下的问题。更何况,如果连纸上的侠士都已消失的话,我们将如何面对那“叹屠龙人杳,屠虎人无,屠狗人遥”的百年孤寂。
好在侠士并未死亡,我是无须过分悲观的,而武侠小说,有武有侠的小说,也仍是千年老树,尚发新枝。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澳大利亚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