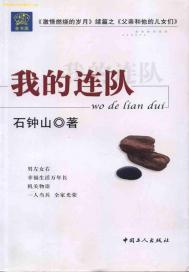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踏踏主义,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有先进国的史实在;要取目前的例,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UptonSinclair,《创造月刊》也背了Vigny在“开步走”了。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着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鲁迅先生:
在《新闻报》的《学海》栏内,读到你底一篇《文学和政治的歧途》的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宁为满足,这满足,在感觉锐敏的文学者看去,一样是胡涂不彻底,表示失望,终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脚。我觉得这是世界各国成为定例的事实。最近又在《语丝》上读到《民众主义和天才》和你底《“醉眼”中的朦胧》两篇文字,确实提醒了此刻现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义和革命文学的迷梦的人们之朦胧不少,至少在我是这样。
我相信文艺思潮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这是说,文艺之流,从最初的什么主义到现在的什么主义,所写着的内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练的才技,造成一篇优美无媲的文艺作品,终是一样。一条长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现的形相,虽然不同,而长江还是一条长江。我们看它那下流的广大深缓,足以灌田亩,驶巨舶,便忘记了给它形成这广大深缓的来源,已觉糊涂到透顶。若再断章取义,说:此刻现在,我们所要的是长江的下流,因为可以利用,增加我们的财富,上流的长江可以不要,有着简直无用。这是完全以经济价值去评断长江本身整个的价值了。这种评断,出于着眼在经济价值的商人之口,不足为怪;出于着眼在艺术价值的文艺家之口,未免昏乱至于无可救药了。因为拿艺术价值去评断长江之上流,未始没有意义,或竟比之下流较为自然奇伟,也未可知。
真与美是构成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的两大要素。而构成这真与美至于最高等级,便是造成一件艺术品,使它含有最高级的艺术价值,那便非赖最高级的天才不可了。如果这个论断可以否认,那末我们为什么称颂荷马,但丁,沙士比亚和歌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和他们同等的文艺作品呢,我们也有观察现象的眼,有运用文思的脑,有握管伸纸的手?
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由此说,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
我觉得许多提倡革命文学的所谓革命文艺家,也许是把表现人生这句话误解了。他们也许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的文艺,所表现的都是现实的人生,在那里面,含有显着的时代精神。文艺家自惊醒了所谓“象牙之塔”的梦以后,都应该跟着时代环境奔走;离开时代而创造文艺,便是独善主义或贵族主义的文艺了。他们看到易卜生之伟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国革命时期内的作家叶遂宁和戈理基们的热切动人;便以为现在此后的文艺家都须拿当时的生活现象来诅咒,刻划,予社会以改造革命的机会,使文艺变为民众的和革命的文艺。生在所谓“世纪末”的现代社会里面的人,除非是神经麻木了的,未始不会感到苦闷和悲哀。文艺家终比一般人感觉锐敏一点。摆在他们眼前的既是这么一个社会,蕴在他们心中的当有怎么一种情绪呢!他们有表现或刻划的才技,他们便要如实地写了出来,便无意地成为这时代的社会的呼声了。然而他们还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艺术,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称颂为改革社会的先驱,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称为人道主义的极致者,还须赖他们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经几个真知灼见的批评者为之阐扬而后可。然而,真能懂得他们的艺术的,究竟还是少数。至于叶遂宁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说了,戈理基呢,听人说,已有点灰色了。这且不说。便是以艺术本身而论,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讥笑那不切实的诗人的诗。况且我们以艺术价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还是疑问呵。
实在说,文艺家是不会抛弃社会的,他们是站在民众里面的。有一位否认有条件的文艺批评者,对于泰奴(Taine)的时间条件,认为不确,其理由是:文艺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艺家,还是站在那时候,以那时候的生活环境做地盘而出发,所以他毕竟是那时候的民众之一员,而能在朦胧平安中看出残缺和破败。他们便以熟练的才技,写出这种残缺和破败,于艺术上达到高级的价值为止,在他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创造时,他们也许只顾到艺术的精细微妙,并没想到如何激动民众,予民众以强烈的刺激,使他们血脉愤张,而从事于革命。
我们如果承认艺术有独立的无限的价值,艺术家有完成艺术本身最终目的之必要,那末我们便不能而且不应该撇开艺术价值去指摘艺术家的态度,这和拿艺术家的现实行为去评断他的艺术作品者一样可笑。波特来耳的诗并不因他的狂放而稍减其价值。浅薄者许要咒他为人群的蛇蝎,却不知道他底厌弃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我们平常讥刺一个人,还须观察到他的深处,否则便见得浮薄可鄙。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标准,既没有看到他的深处,又抛弃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尺度,便无的放矢地攻刺一个忠于艺术的人,真的糊涂呢还是别有用意!这不过使我们觉到此刻现在的中国文艺界真不值一谈,因为以批评成名而又是创造自许的所谓文艺家者,还是这样地崇奉功利主义呵!我——自然不是什么文艺家——喜欢读些高级的文艺作品,颇多古旧的东西,很有人说这是迷旧的时代摈弃者。他们告诉我,现在是民众文艺当世了,崭新的专为第四阶级玩味的文艺当世了。我为之愕然者久之,便问他们:民众文艺怎样写法?文艺家用什么手段,使民众都能玩味?现在民众文艺已产生了若干部?革了命之后的民众能够赏识所谓民众文艺者已有几分之几?莫非现在有许多新《三字经》,或新《神童诗》出版了么?我真不知民众化的文艺如何化法,化在内容呢,那我们本有表现民众生活的文艺了的;化在技艺上吧,那末一首国民革命歌尽够充数了,你听:“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多么宏壮而明白呵!我们为什么还要别的文艺?他们不能明确地回答,而我也糊涂到而今。此刻现在,才从《民众主义与天才》一文里得了答案,是:“无论民众艺术如何地主张艺术的普遍性或平等性,但艺术作品无论如何自有无限的价值等差,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所谓普遍性啦,平等性啦这一类话,意思不外乎是说艺术的内容是关于广众的民间生活或关于人生的普遍事象,而有这种内容的艺术,始可以供给一般民众的玩味。艺术备有像这种意味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不待说是不可以否认的,然而艺术作品既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以上,那些比较高级的艺术品,好,就可以说多少能够供给一般民众的玩味,若要说一切人都能够一样的精细,一样的深刻,一样的微妙——换句话说,绝对平等的来玩味它,那无论如何是不得有的事实。”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最先进的思想只有站在最高层的先进的少数人能够了解,等到这种思想透入群众里去的时候,已经不是先进的思想了。这些话,是告诉我们芸芸众生,到底有一大部分感觉不敏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不平等,除了诅咒造物的不公,我们还能怨谁呢?这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人类的演进史,可以一笔抹杀,而革命也不能发生了。世界文化的推进,全赖少数先觉之冲锋陷阵,如果各个人的聪明才智,都是相等,文化也早就发达到极致了,世界也就大同了,所谓“螺旋式进行”一句话,还不是等于废话?艺术是文化的一部,文化有进退,艺术自不能除外。民众化的艺术,以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差来说,简直不能成立。自然,借文艺以革命这梦呓,也终究是一种梦呓罢了!以上是我的意思,未知先生以为如何?
一九二八,三,二五,冬芬。
回信
冬芬先生:
我不是批评家,因此也不是艺术家,因为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至少,在现在的上海滩上。因为并非艺术家,所以并不以为艺术特别崇高,正如自己不卖膏药,便不来打拳赞药一样。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人类如果进步,则无论他所写的是外表,是内心,总要陈旧,以至灭亡的。不过近来的批评家,似乎很怕这两个字,只想在文学上成仙。
各种主义的名称的勃兴,也是必然的现象。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虽然有许多在受难,但也有多少占权,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文学。
中国的批评界怎样的趋势,我却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有的说要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几句短短的冷话。还有,是自己摆着文艺批评家的架子,而憎恶别人的鼓吹了创作。倘无创作,将批评什么呢,这是我最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肠的。
别的此刻不谈。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
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
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看两句冯乃超的剧本的结末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四月四日。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