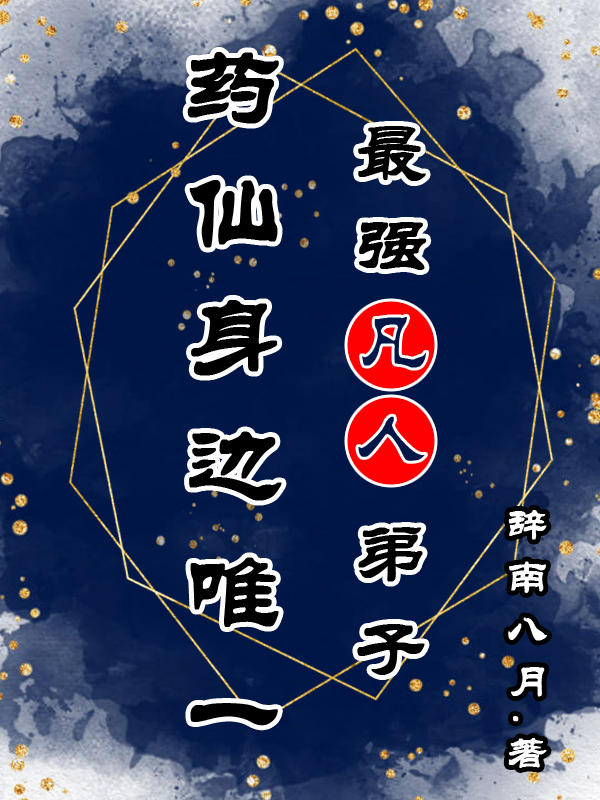鲜花、贵宾、收藏,尽量地砸呀!燕歌需要你们的支持!
……
月色下这位绝色少女,面容楚楚,就要送给恶鬼般的杨志诚,李贤齐胸中涌出一股豪情,为她轻轻拢好衣衫,“某带你逃出北风峪,只要出了谷口,我家势力不小,你阿爸也不敢得罪我们。”
“他会不会将怒气撒到我娘头上?”玉娘眉头微蹙,担忧道。
“两家成了亲戚,他不会怪罪你娘,嗯,要不然将你娘一块带走,阿布思顿贺没有住在你娘那儿吧?” 李贤齐问道。
玉娘摇头否决,“他那么多妻妾,我娘一年难得见上她几回。”
“待会到马厩牵两匹好马,那两匹大食马不错,刚好我们四骑出谷,到谷外汇合红巾儿就安全了。” 李贤齐话语中不露一丝盗马的意图。
玉娘高兴得几乎要喊出来,“那就牵夜月和墨龙,夜月驹温驯听话,墨龙驹脾气暴躁,除了刘武先外,只有奴骑过它?”
“你的骑术有那么好?” 李贤齐吃惊,牝马难驯,往往要阉割后才可作为战马。
玉娘垂首叹道:“奴和两匹马儿一样的命运,都要被当做礼物送人,同病相怜,奴常到马厩给它们喂食,陪它们说话、刷马……这会儿又该给马儿喂食了。”
玉娘从马夫那儿取来一升豆子,想来平日她常干这事,马夫也未生疑。
墨龙驹看见李贤齐过来,警惕地瞪着他,左右拽着缰绳,动个不停,玉娘捧起一把豆子,站在墨龙驹前面,一边喂食,一边同它低声说着话,不时还转头望着正给夜月喂食的李贤齐。
墨龙驹极有灵性,低低地嘶鸣一声,表示它已听懂了,慢慢安静下来。
玉娘去接她母亲,李贤齐继续给青骓马和周武那匹特勒骠喂豆子,等着她们。
北风峪的灯火渐渐熄灭,纵情歌舞了大半宿,疲累的人们都宽衣就寝了,天地间只有皎洁如银的月色,缓缓在山谷流淌,李贤齐扳鞍认蹬,翻身上了夜月驹的马背,玉娘骑着墨龙驹,两人在前面开路,周武和玉娘母亲远远地吊在后面。
难得玉娘心细,与她母亲用白叠布紧裹住马蹄,四匹马儿蹄飞踏燕,却是无声,山风呼呼地从李贤齐耳边挂过,墨龙驹和夜月驹如月下的精灵,风驰电挚一般在山谷飞奔。
只要过了谷口那道险峻的关隘,天高任鸟飞,红巾儿连夜从雁栖湖撤走,想来阿布思顿贺权衡一番,也不会昏了头翻脸追杀。
上半夜都还开着的关门此时紧闭,那些在湖畔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也不回谷了,就在雁栖湖畔相依相偎一夜?
望着阴影中的关隘,李贤齐紧皱眉头,人算不如天算,难道插翅飞过去不成?诈门出关,守关的狼盗看见两匹大食名驹,什么都明白了。强攻突袭,只有自己和周武俩人。趁着狼盗疲累摸哨,胁迫他们打开关门……稍一不慎,自身难保不说,还要殃及玉娘和她母亲?
李贤齐与玉娘松开缰绳,在一处小山坳轻轻勒住马缰,等周武和玉娘的母亲赶来。
“怎么也没料到关门紧闭,玉娘,和你母亲在这儿等着,某和周武去赚开关门。一见火把划圈或听见唿哨声你们就快马冲关。”李贤齐取弓在手,悄声吩咐。
“我们可以驱马下河,揪着马尾巴顺流而下,到了雁栖湖才上岸。” 玉娘眨着湖水般清澈深邃的眼睛建议。
“进谷时某已瞧过,水流湍急,溪石错乱,太危险了。” 李贤齐摇头,眼下无计可施,只有摸关偷袭这一条道了。
几人正在商议,遥见关隘灯火通明,隐隐有争吵的声音传来,李贤齐起初一惊,难道这么快阿布思顿贺就发现了战马被盗,在山坳中等了一会,却无人搜查过来,恐怕关隘另有变故。
“玉娘你们在这等着,我们过去瞧瞧。”李贤齐与周武借助树木的阴影,兔起鹘落,悄悄掩近了关隘。
一个嚣张的声音从关隘前传来:“一群窝在山谷里的兔子,瞧你们胆小如鼠的模样,刘堂主率狼盗大胜血刀帮,好心给你们报个信,也不让爷进关歇歇脚,老子数到十,还不大开关门迎接。哼,吐迷儿,你就如同那灯笼——”
话音未落,“咻!”的一声,高挂在望楼的一盏红灯笼被射落在地。
关隘上,守关的头目吐迷儿怒道:“麻脸,你少在老子面前耍横,阿堂主有令,夜晚打开关门须有他的手令,盐栖湖畔有几顶营帐,你们过去挤挤。”
“……五,六!”在关隘前的麻脸极不耐烦。
吐迷儿突地像被谁推了一把,“哎哟”痛叫一声,身子向前扑了一步,右肩赫然插着一枝从后面飞来的羽箭。
肯定是暗中追随刘堂主的狼盗下黑手,麻脸见状狞笑,“吐迷儿,有好几张弓指着你呢,八,九!”
吐迷儿四下张望,不知关隘后那片阴影中藏了几位刘武先的手下,里应外合之势已成,额头渗出黄豆大的汗珠,吐迷儿心中恐慌,想来阿堂主已有了应对,自己也犯不着在这儿死撑……再也承受不了这如山般的压力,蓦地喝道:“开关门,迎接兄弟回谷!”
周武取了枝火把划了个圈,玉娘与她母亲策马飞驰过来。
刚推开关隘的大门,关内有人大声赞道:“刘堂主出马,果然威风,从此幽燕无人敢小瞧我北风堂!”
“兄弟们辛苦,阿堂主命我等出关迎接!”几骑如一阵风刮出了寨门,迎着关隘前麻脸那几骑狼盗而去,月光将关隘前照得如同白昼,李贤齐心神锁定狼盗,张弓松弦,三枝风羽箭快如闪电,激射而出。
麻脸一眼瞧见率先冲出堡门的夜月驹,难道是阿堂主亲至,心中发虚,毕恭毕敬在马上拱手见礼,“参见阿布思堂主——啊”
惨叫一声,已被一箭穿额,“轰”地一声从马上栽倒。
周武跟着顺鬃直射,也是箭不虚发。
十来枝快箭如水连珠般迎面扑来,几名狼盗中箭翻落马下。
墨龙驹冲过来,嘶鸣一声,那几匹战马竟不恋主,跟着墨龙驹一道奔向雁栖湖畔。
大食名驹终于到手!李贤齐心中涌起一阵狂喜。
关隘后传来一阵密如骤雨的马蹄声,李贤齐脸色一变,急令周武:“周武,护着玉娘和她母亲,快马去营帐召集红巾儿迎敌,某来阻敌断后。”
李贤齐勒马回转,缓驰向前迎敌,右手摸出三枝风羽箭,张弓、搭箭、松弦,三枝风羽箭又快又急,朝门洞疾飞而去,马不停,手上也没有闲着,又是三枝风羽箭搭上弓弦……前面几骑刚出关门不远,被突然而至的风羽箭射中,或死或伤,乱成一团。
李贤齐驻马停下,前面十几步远的地方,横七竖八地躺着麻脸带来的狼盗,一两个中箭倒地未死的还在大声**。
李贤齐胯下是神俊高大的夜月驹,皮甲红巾,披一身皎洁如银的月色,盘马弯弓,凛然暴喝:“敢出关追击者死!”
忽地关隘城头涌出一大群狼盗,如众星拱月般拥着阿布思顿贺,熊熊燃烧的火把照耀下,亮如白昼,一个个狼盗张弓搭箭,怒目相向。
阿布思顿贺仔细瞧了一会,忽地拍掌大笑:“兄弟们,都放下弓箭,公子好俊的身手,夜盗名马美人,一骑快箭退敌,让北风峪上下乱了方寸,不愧出自幽州将门,公子就是阿布思顿贺亲自选的乘龙快婿。”
为安全计,李贤齐策马悄悄退了十来步,厚着脸皮,笑着吆喝:“老丈人干的是没本钱买卖,女婿也没给你老人家丢脸,顺手牵几匹马走,当作玉娘的嫁妆,可好?”
“贤婿,那点儿嫁妆怎么够?既然成了翁婿,就不是外人,我们坐下来商议商议酒马互市?” 阿布思顿贺一口一个贤婿亲热叫着,可能觉得是一窝狐狸不嫌骚。
湖畔响起了急促刺耳的骨笛声,连续三声催得紧,李贤齐心知红巾儿已做好准备,执弓拱手道:“老丈人且放宽心,后年某带着外孙来北风峪看望你老人家,再来详谈酒马互市,今晚你若派人相送,某也会让他们披红挂彩,沾点喜气,告辞!”
李贤齐转身策马离去,一骑绝尘,夜月驹仿佛一片凝结的月光,融入了茫茫月色。
阿布思顿贺在关隘上急得直跺脚,“备马,某一骑追上去,酒马互市关乎北风堂将来的生存发展,万不可错失良机。”
吐迷儿已裹好伤,肩上缠着绷带,也不顾疼痛:“堂主,某随你去。”
阿布思顿贺点头应允,扫视着关隘上的狼盗,“你们留在关内,马不卸鞍,人不离甲,做好战斗准备,有甚事吐迷儿会回来传令。”
狼盗们轰然应诺,目送着阿布思顿贺和吐迷儿两骑出关。
阿布思顿贺的声音随着浩荡的山风传来,“将关隘前受伤的兄弟抬回去……敷药裹伤。”
李贤齐汇合了红巾儿,率军匆匆进入一片山坡上的树林,潜藏下来,环顾左右道:“阿布思顿贺以为我盗马得手,必然远遁,某率红巾儿潜伏在这儿,仅以少量游哨断后,迷惑狼盗,待他们追出谷,我等从后掩杀,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是这个道理。”
周围的红巾儿恭谨受教。
李贤齐警惕之心未减,思索片刻,草草拟就一封书信,“周武,你快马赶往檀州,向雄武军使张仲武借几百越骑,如果狼盗不识好歹,尾随堵截红巾儿,就一举将它除之,顺便占了北风峪,嗯。我们以骨笛传讯,相互配合。”
周武接令,率几骑红巾儿向檀州驰去。
断后的红巾儿游哨回报:“禀巨子,北风峪只有两骑追出,已被生擒,乃是阿布思顿贺和一名受伤的头目。”
“瞧瞧去。”李贤齐催马来到树林边,擒贼先擒王,阿布思顿贺既然擒在手中,又有何惧?
……
李贤齐夜盗美人儿名马,盘马弯弓,月下退敌,如果你觉得精彩,投票收藏吧!